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常见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的精神疾病,多起病于青壮年,常有特殊的思维、知觉、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和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本病早期恰当治疗可获得较好疗效,但康复时期患者的病耻感严重影响着病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及生存质量。近年来随着精神病学临床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心理学研究的进步,使得医生不仅仅停留在治疗精神症状上,正越来越重视患者的心理康复状况,从患者的心理方面和环境方面对病耻感关注和评估,为精神病人更好康复和回归提供重要帮助。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较多的精神分裂症病耻感的相关研究,笔者对近年此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1. 病耻感的概念和病耻感的评估
病耻感( stigma) 一词的原意为“烙印”, 即烙在奴隶或囚犯身上的标记, 是一种外界加诸个体身上的耻辱的标志。精神病人常常遭受自我的耻感和面临社会的耻感[1],第一:他们必须要应付疾病本身的种种症状,如因脑部功能紊乱而反复出现的幻觉、妄想、焦虑或情绪不稳定,这些症状使病人很难从事工作、独立生活、过上有品质的满意的生活。第二:社会对精神病人的误解,即使有些病人将自己的疾病管理得非常好,以至于能顺利胜任工作,但由于雇主的歧视,仍有巨大的困难而找不到工作。如此精神病患者不仅症状引起耻感,又要遭受社会上一系列的消极对待,多数精神病患者接受对精神病的歧视偏见,使他们自己痛恨自己,同时失去信心,后者称为“自我的病耻感”。最初对病耻感的研究是2001年-BG等[2]通过设计各种问卷来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对象不同分为患者问卷和普通人问卷;根据评估内容的不同又分为感受问卷和经历问卷,该研究根据病耻感的标签理论设计了一套-量表,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评价排斥和歧视:共有12个条目(包括收入、职业状况、社会支持、自信心、生活质量、抑郁症状、寻求帮助及自我评价内容);第二部分评价对病耻感的应付行为(包括回避交往、隐瞒病情、应付病耻感的行为在同伴中互相传播等);第三部分评价与病耻感相关的心理体验,由两个分量表组成(1.担心被别人误解,患者始终担心因为曾经住进精神病院而被别人另眼看待,2.羞辱感和与他人异样感,患者觉得自己的精神病体验或住院经历与其他人产生了隔阂,并且为此感到羞辱)。2003年 Ritsher, J.B.等[3]研究小组在美国构建了精神疾病病耻感量表(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scale,ISMI),主要用以评价精神病患者的主观体验。量表包含29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5个维度:疏远、刻板印象的认可、歧视经历、社交回避和对抗病耻感。研究显示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ISMI对病耻感的测量包括了“感知的病耻感”和“实际的病耻感”量表还加入了正性情感体验的条目,用以评价患者对抗病耻感的态度和想法。 国内曾庆枝等[4]在文献复习、重点人群访谈、专家评阅和预调查的基础上,采用Likert4点格式编制病耻感评估量表,并抽取460例精神病住院、门诊和康复患者,对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论显示了该病耻感量表的信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结构较合理,该量表的制定有助于国内研究者理解和评估精神病人的歧视体验。随着病耻感评估工具日渐成熟,精神科医生与临床心理医生对精神病人病耻感的重视和研究将成为新的热点,这将有助于减轻病人的心理负担,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生活质量。
2. 精神分裂症的病耻感
有文献报告精神分裂症与情感性精神病的比较研究,亦有精神分裂症与糖尿病的对照研究,均显示精神分裂症的病耻感最为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更深的耻感体验、他们对病情隐蔽、不配合治疗、由于更易受到雇主、同行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拒绝而丧失工作机会,尽管有较高的学历也比其他疾病更容易遭受单身、失业、低收入,这样便放大了病耻感的影响[5]。精神疾病中精神分裂症属重性精神病,因多数患者有反复发作且预后不佳而遭歧视、排斥、被人看不起、抬不起头来,这种感受的病耻无论是在院内还是院外,即使在缺乏直接歧视的环境下亦可产生, 是患者的一种内化的消极体验,即病耻感( stigma)。Corrigan等[6]称这种态度和行为是内在化的病耻感。其实,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偏见、误解现象早已存在,但关于精神疾病的病耻感的重视则最早来源于社会学家Goffman,而非精神病学家[7、8]。为了描述和理解病耻感Ritsher[3]教授于2003年采用5因子法来度量病耻感的水平,发现精神病人除有精神病以外还普遍存在对患有疾病的病耻感。近10年来,国内外有不少精神病学家对此给予关注:Jennifer Boyd Ritshera[9]和Sartorius N[10]研究门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康复期普遍存在病耻感。Prince[11]在研究精神病患者的自我耻感时发现有73.2%经常感觉自我贬值和被歧视。Jennifer Boyd Ritshera[9]对82例门诊精神科患者研究并进行4月的随访发现有1/3的患者存在高水平耻感并可达抑郁标准,约2/5的报告提示社会退缩,仅有1/4 的受试者有高水平的耻辱抵抗信念。Schulze B等[12]研究发现:对25例德国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实质性访谈发现49%患者陈述在与人交往中受到歧视,有病耻感的主观感受。Chee CYI等[13]研究新加坡的普通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的600例精神病患者发现:48.6%的患者认为别人会贬低他们,37.1%患者感到羞耻,59.2%的患者在找工作时遭到歧视,38.8%的患者认为他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病情会避开他。
国内陈熠等[14]利用家属病耻感访谈问卷(Family Stigma Interview,FSI)调查了72 例重性精神病患者家属,发现普遍存在病耻感,尤其是患者的子女及教育程度较高者。2005 年高士元等[15]在北京3 家精神病专科医院抽取了225 例缓解期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属调查,结果显示42%患者经历过单位不公正的对待, 56%的家属为避免歧视隐瞒病人患精神病的事实。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黄佩蓉[16]对209名住院时间12个月以上的精神病患者调查发现普遍存在病耻感。Phillips 等[17]1990~2000 年在中国大陆5 个精神卫生机构使用坎伯威家属访谈问卷(Camberwell Family Interview,CFI) 对1491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家属进行病耻感的评估, 60%的患者及家属认为他们的生活因病耻感受到中等程度以上的影响。
尽管国外与国内研究方法和对象的选择及对病耻感的理解不尽相同,得出的数据也有差异,但都无一例外地证实了精神病患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的现实性和严重性。
3.病耻感来源及相关因素
众所周知,全球范围内由精神疾病引起的歧视及病耻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Corrigan PW[18]对病耻感理解为一种在主流人群与承受病耻的次级人群间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差异,系统调节的动物模型以朴素心理学理论为基础,把病耻感来自对精神病人的害怕以及认为他们是理当受谴责的两种认知综合起来,作为精神病人受歧视的根本原因。Allison Bolger Carlisle[19]对产生病耻感理解为原罪的疯狂:否则精神病治疗为何给患者带来病耻感?这是许多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正在分析精神病患者病耻感的根源,并试图寻求解决途径。Allison的研究认为由于精神疾病本身被定义为“坏”的,所以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也因此被定义为有问题的。只有当对该诊断名称的负性评价被消除后,病耻感才有可能消除。有人认为精神病人的歧视可能属于某种人类与生俱来的观念,可以从儿童期一直持续到成年,与时代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没有直接关系。这些说法显然不够全面,新进的研究揭示了产生病耻感的因素不仅来自患者本人消极感受、经历的被羞耻经验、治疗相关的耻感以及结构的歧视[20]。患者本身的耻感由于发生精神异常时是被同学、老师或家长发现,有了被强行住院接受自己不认可的“治疗和护理”自感人格被耻辱、不公平和歧视的待遇的经历,即使在以后恢复了自知力的长期治疗过程中,病人仍担心被人知道而异地就诊;不敢请病假而请年休假;住院时拒绝探望;要求医生帮助隐藏或为他们的诊断保密。最近Freudenreich等的研究显示精神病分裂症的病人存在药物感应的病耻感和治疗的不依从[21] 。病人在服药治疗中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病人身份,掩饰药物的副作用可能常常拒绝服药或推迟治疗。病耻感还可发生于社会和同事对自己的除危险和指责外,还有认为精神病人不负责任,无能,无常,孩子气,或者精神病会传染等成见。恐惧:因为他们有暴力的潜在可能,患有精神病的人是令人害怕的;愤怒:患有精神病的人逃避许多成人应该承担的责任,所以是应该令众人愤怒的;可怜:患有精神病的人令人同情;厌恶:在内心世界,患有精神病的人是令人厌恶的等偏见和强迫(强制治疗),回避(不给予工作和独立居住的机会)等等。此外还有把社会资源和服务老套地提供给其它人等等负性行为,均与病耻感的产生有关。
4.病耻感对治疗依从性及生存质量的影响
国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病耻感和被歧视会导致慢性社会功能降低,会影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但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有病耻感的精神病人,他们为自己保密、自我封闭、否定自身价值和自我尊重、丧失治疗最佳时机,另一方面可能为此产生逆反心理,拒绝接受将被贬低的社会地位,否认有病,成为特殊性质的社会人,可导致社会适应困难和接受治疗时依从性差,这是病情复发、病情加重或慢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是多数患者的预后不良的结果。Rusch N [22]在不同精神疾病患者中展开的研究结果显示病耻感影响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寻求治疗的行为、自尊和社会适应功能。该研究认为关键因素是治疗的副反应,但主要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患者害怕经过治疗后会被贴上“精神病”的标记,受到歧视,于是便不接受精神卫生服务,试图这样可以避免耻感。Jackowska E [23]对欧洲(波兰、瑞士、德国、克罗地亚和西班牙)几个国家社区居民的公众信念调查和研究证实早期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病耻感会阻止病人的成功治疗,尤其是病耻感负担会导致慢性社会功能降低;该资料也显示病人被诊断精神分裂症,他们的家庭成员、家属也承担着社会的疏远感,不仅在一般公众场合遭到排斥和拒绝,公众的态度:人们往往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具有的危险性、不可预测性、不可靠而担心。从受访者的心理机制上表达了对精神病人的歧视与偏见。 Elaine Brohan等[24]对欧洲14个国家1229例病人采用心理健康的非政府组织成员邮寄问卷调查的方式报告了欧洲的精神病人中41.7%有高水平的自我耻辱,有49.2%的人中度或高度的病耻感抵抗,49.7%的人中度或高度权力被剥夺,69.4%的人不能被理解或被歧视,这些结果表明,有病耻感似乎是共同的,会严重影响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治疗和预后。有社会心理学者从微观的病耻感结构和水平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20]认为:落后的治疗机构和治疗机制提供较差的治疗服务,一定是缺乏心理学的干预手段介入病耻感,才会导致的病耻感和被排斥感。研究中显示有54%的精神分裂症病人住院期间有经历过多种副作用的经验,而明确地说,70%的报告没有解释药物的副作用,超过26%的患者是感到被威胁或欺骗才接受治疗的,近40%的患者经受过过度的身体束缚,毕竟这种不受欢迎的住院治疗经验是不公平的,这些负面的治疗经历都是病人产生结构性病耻感的实例。此外这种病耻感还会蔓延到患者的家庭成员,产生“连带病耻感”,家属的耻辱感和主观悲伤反过来又会影响家庭关系和对患者的态度,进而影响患者的治疗和预后。宋晓红等[25]对500例精神病人进行调查发现:许多精神病患者都面临着精神残疾和病耻感双重挑战,对精神疾病的人而言,病耻感是其提高生活质量的最大障碍。国内徐辉对北京三甲精神病专科医院的116例康复期精神分裂症病人进行1个月和3个月电话随访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普遍存在病耻感,出院后的不依从行为与患者较高的“被误解感”有关,但回归分析发现病耻感对出院后短期的服药依从性没有影响。这种“被误解感”是自知力缺乏还是属于病耻感的体验值得探讨和研究。
5.降低精神病人病耻感的措施
开展促进心理健康和积极健康的策略对驱逐和减轻精神病人的病耻感相当重要[26、27],国际社会一直比较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被歧视问题,为此开展了多项歧视干预项目,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8]。自从1996年世界精神病协会便开始在一些国家开展减轻精神病人病耻和歧视的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6、29],国内各界人士虽然早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仅在香港地区开展相应的研究[30],内地干预性的研究较少。Tsang HW[31]应用社会技能训练为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恢复健康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精神分裂症病人随着精神症状的逐渐消失,自知力的不断恢复,其心理压力也愈加突出,他们面临出院后社会环境的适应和社会功能的恢复,担心未来的前途和婚姻家庭,又要承担他人和社会的歧视。这种“病耻感”使得病人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导致自尊水平的降低,对重返社会缺乏信心,变得自卑、孤僻、甚至与世隔绝、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悲观忧愁、焦虑紧张等,甚至部分病人出现了“自觉羞耻”的现象,病人觉得这比疾病症状本身还要痛苦,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心理、生理及社会的全面康复。据介绍低自尊和降低自我价值感,导致孤独、抑郁、社交焦虑及疏远。该研究发现心理干预及技能训练可提高病人的自尊水平。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精神病研究所健康服务与人口部的Rose[32]教授利用混合的方法和手段对75例来自15个国家的人士进行访谈,以评估病耻感后专题进行分析发现:采用理论上与精神病患者多接触的方式来减少病人的耻辱感和歧视的结果并不完全受到支持。Wolfgang Gaebel[33] 从德国“打开门户”运动中得出经验,对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的调查和早期干预不仅可以减轻病耻感,还对提高治疗效果和生存质量有极大帮助。WPA开展国际性“打开门户”运动反对精神分裂症相关的歧视和病耻感。在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很多国家反病耻感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主要干预措施有3种:抗议活动、公众教育和与患者接触。不同国家多种干预途径显示:抗议运动只在短期内改善了人们的偏见和歧视,公众教育也仅仅改变了公众关于精神疾病的知识,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改变甚微,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反而有根强烈的消极态度和排斥行为。 GORO TANAKA等[34]认为增强对精神分裂症的认识的转变可以降低精神病人的病耻感: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疾病,它的可被治疗性越来越有积极意义,这也显示了这种观点加入到指定的教育项目中,增加病人的疾病意识和知识即精神疾病是一种自然疾病是可以治疗的观点。而Thompzon 等[35]调查加拿大三个城市的反病耻感运动情况显示:反病耻感运动没有显示出有效性,仅对于一些认知,如危险性的认识有所改善,毕竟精神分裂症不能彻底治愈。亚洲的日本GORO TANAKA[36] 在评估人们对病耻感的态度及相关因素中强调:对精神病人中的重点群体(如高学历)针对性地列出重点项目,通过精心设计的教育项目对先前有过接触的、乐于从事到自愿者队伍中积极活动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远远比仅通过服用药物治疗要好得多,可大大减轻病耻感。整理和发展这些影响因子能够给精神病人和家属带来希望,增加对公众对预防精神疾病、治疗可行性、可治愈性、尊重人权、减少治疗环节障碍和护理的障碍可显著减轻病耻感,除此之外没有治愈的奇迹。中国香港的Lee S等[30]在分析病耻感结构组成、环境、条件等产生机制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精神病药物机制的耻感,提示切实可行地减少服用传统抗精神病药物引起的副反应,减轻药物导致的在社会上“被识别”所带来的耻感。
小结
国内外较多研究证实精神病人存在病耻感,流行病学的调查和临床心理医生一致认为重型精神病病耻感更加强烈,尤其是精神分裂症。近年来国外的研究日趋活跃,虽然国内外对病耻感概念的理解的多样性导致病耻感测量工具的不统一,不同的测量工具有时存在差异,但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的评估工具也日渐成熟。国内外研究一致证实:病耻感影响患者的后续治疗的依从性和回归社会,是精神病人提高生存质量的严重障碍,精神病患者都面临着精神残疾和病耻感(疾病耻辱感)双重挑战,如何把精神病人的病耻感作为一个定向的、有价值的观察指标是临床医生评估疗效的目标。采取何种方式、如何进行更加有效的心理干预是精神科医生和心理科医生的新挑战。我们将来试着采取持续干预的方式来研究病耻感意义重大。对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期患者采取分成的干预措施可能收效更好,值得我们需要验证的是:是否热情开朗、财政收入好身体好、又能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是产生低病耻感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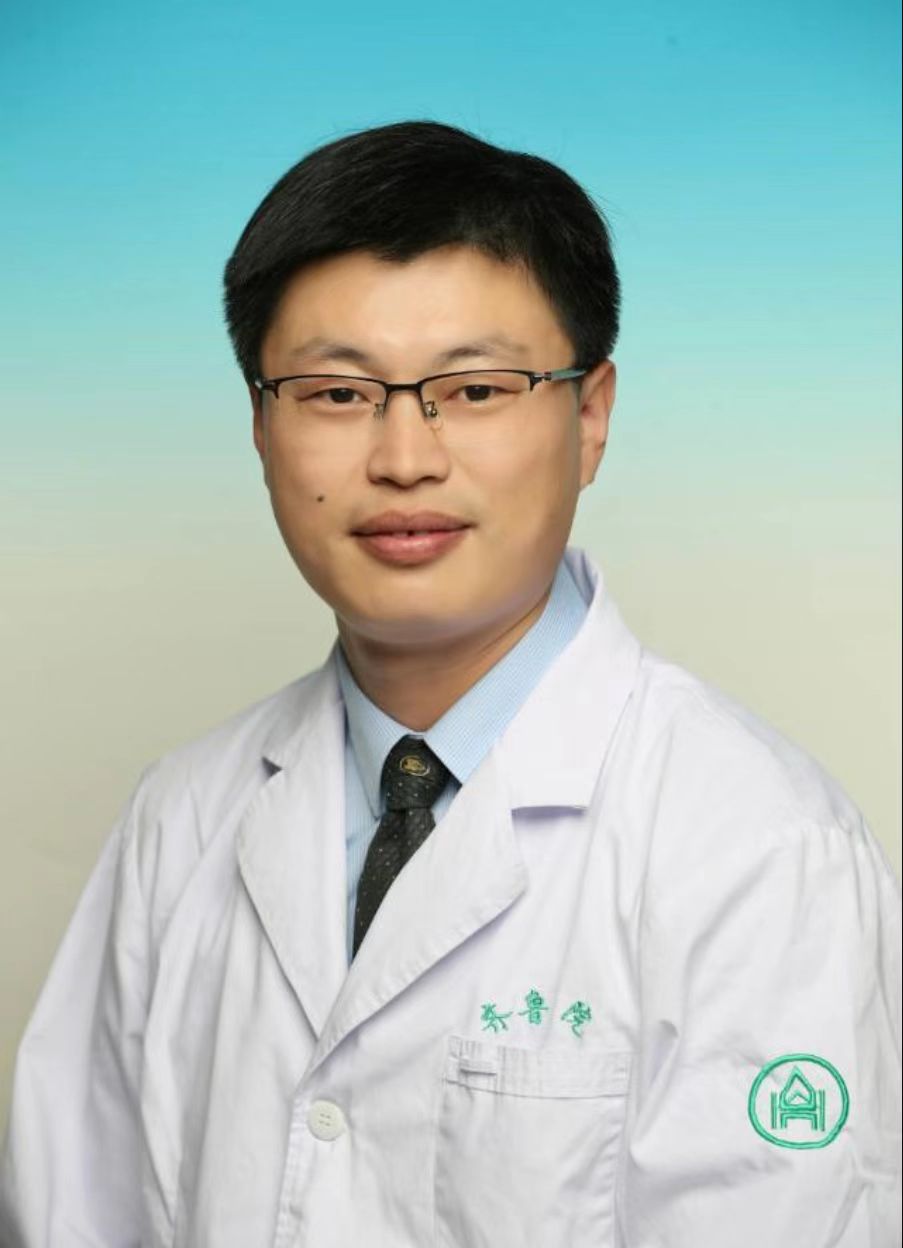 杨乐金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主任医师心理咨询科
杨乐金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副主任医师心理咨询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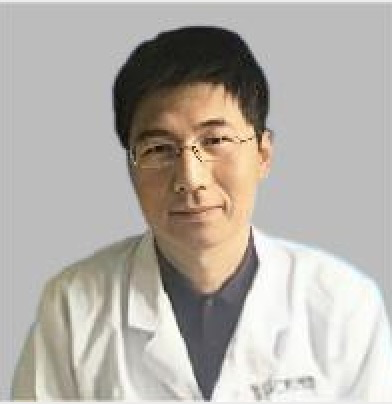 宋观礼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医科
宋观礼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副主任医师中医科
 刘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精神科
刘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精神科
 陈博浙江衢化医院主治医师中医科
陈博浙江衢化医院主治医师中医科
 姜红燕云大医院副主任医师精神科
姜红燕云大医院副主任医师精神科
 王晓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医院主任医师神经外科
王晓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医院主任医师神经外科